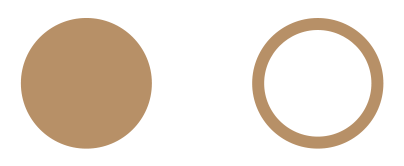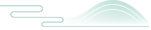“湖湘”:三重地理标识的意义
“湖湘”作为一个文化地理的概念较早就出现于唐代,但它是以自然地理与行政地理为先在条件的。[1]周振鹤先生曾经指出,“对于中国历史上自然区域、行政区域以及文化区域三者相互关系的研究,是一个尚待开拓的研究课题。”[2]他强调,这三者的关系,对于文化区的重新塑造十分重要。
本文着重讨论“湖湘”作为区域文化概念的形成过程。我们会发现,“湖湘”最初只是一个自然地理的概念,然后才形成相关的行政地理、文化地理的概念,体现出三者之间密不可分的内在联系。
“湖”、“湘”本来只是自然地理的概念。“湖”是指洞庭湖,它是中国的著名的“五湖”之一,以湖心的君山岛古称“洞庭”而得名。洞庭湖烟波浩淼,有八百里洞庭之称,以至于有人称“四渎长江为长,五湖洞庭为先”。由于洞庭湖的规模很大,故而成为中南地区的重要自然地理标识。而“湘”则是指湘江,现在的湖南省内由西、南汇入洞庭湖的有湘、资、沅、澧四条江水,其中以湘江最长。湘江发源于湖南蓝山县[3],流经永州、衡阳、湘潭、长沙、岳阳,是贯穿湖南地区的主要河流,故而也成为湖南地区的主要自然地理的标识。洞庭湖、湘江作为湖南地区两个重要的自然地理现象,其命名也产生很早。在战国时期的一些重要文献中,早就出现了关于洞庭湖、湘江的名称。据先秦的文献记载:
又东南一百二十里,曰洞庭之山。……帝之二女居之,是常 游于江渊。澧沅之风,交潇湘之渊,是九江之间。[4]
袅袅兮秋风,洞庭波兮木叶下。[5]
浩浩沅湘,分流汩兮。[6]
可见,至少在战国时期,洞庭湖、湘江就作为标志性自然地理的名称大量出现在当时的诗文之中。而且,由于洞庭湖、湘江是两个最终合为一体的自然现象,这些诗文也往往是将“洞庭”与“湘”的名字联系在一起讲的。
“湖”、“湘”又是人文地理的概念。人总是在自然条件下创造出文化来,特别是洞庭湖、湘江这样重要的自然地理标识,总是与人文历史密切相关,故而又成为重要的人文地理标识。前面所引《山海经》、《楚辞》关于洞庭湖、潇湘、沅湘的记载,就与这个区域的神话传说、宗教信仰、文学艺术的人文现象联系在一起。所以,在历史上,人们一讲到洞庭、湘江,总会联想起与这些自然标识紧密相联系的人文现象:湘君、湘夫人的神话传说,舜帝与湘妃的爱情故事,忠贞不屈的三闾大夫屈原与他吟唱的《九章》、《九歌》、《离骚》,思考身心性命的宋代湖湘学派,倡导经世致用的清代湘学,等等。也就是说,洞庭湖、湘江这些自然地理概念,又成了重要的人文地理概念。
在上述自然、人文的基础之上,“湖”、“湘”又成为一个行政地理的概念。中国古代行政区域的确立、命名往往是以自然为标识而确立的,尤其是省区的命名大多与一些自然地理的标识有关,譬如黄河(河北、河南)、太行山(山西、山东)、洞庭湖(湖南、湖北)。由于不同的自然地理条件又会影响到文化区域的产生,所以,传统中国的行政区域基本上是以自然地理、文化地理为依据建立起来的。这样,洞庭湖、湘江又成为郡省及其下属行政单位命名的依据。根据2002年在湖南龙山县里耶镇出土的秦简记载,秦所设的郡级行政单位就有“洞庭郡”。西晋时期,设立以“湘”命名的“湘州”,统领长沙、衡阳、湘东、零陵、邵陵、桂阳等郡。唐以后,“湘州”的轄区又被一个新的“湖南观察使”所统轄。所以,清初湖南成为独立的行政省区时,就以“湖南”命名,一直沿用至今,并以“湘”作为湖南省的简称。总之,“湖”、“湘”又是一个行政地理的标识。
由上可见,“湖湘”既是自然地理的概念,又是文化地理、行政地理的概念,而且这三者是密切关联的。“湖湘”作为人文地理概念总是与自然地理、行政地理的“湖湘”密切相关的。探讨湖南的自然地理、行政地理与文化地理的互动关系,对把握“湖湘文化”的历史演变与区域建构十分重要。
2
楚汉时期湖南的文化地理概念:南楚、沅湘
“湖湘”的文化地理概念与“湖南”的行政地理概念是密切关联的,它们同时产生于唐代。但是,在此之前,出现过与“湖湘”相关的文化地理、行政地理的概念。所以,我们首先探讨“湖湘”出现之前的文化地理概念。
战国以前,湖南地区是不同氏族部落居住、活动的地方,尚未纳入古代王国的行政区域,其文化也是与行政地理无关的部族文化,具体来说包括三苗、南蛮、百越等氏族部落,人们统称苗蛮文化。春秋中后期,楚人南下湖南地区,促进了楚文化与苗蛮文化的融合。到了战国初期,湖南地区正式纳入楚国的管辖范围,并设立了行政区。根据《史记》记载苏秦所说:“楚,天下之强国也;王,天下之贤王也。西有黔中、巫郡,东有夏州、海阳,南有洞庭、苍梧,北有陉塞、郇阳。”[7]学者们考证,这里所说的“南有洞庭、苍梧”,即是楚国在南部地区设置的洞庭郡和苍梧郡。[8]洞庭郡一直沿续到秦朝,龙山县出土的里耶秦简中就有“洞庭郡”的记载。可见,洞庭湖的“洞庭”最早就成为楚国的行政区名号。
同时,湘、沅二江也成为这段时期重要的行政区域的名称。在秦汉时期,湘、沅主要是作为县级区域的命名,如秦汉时期设置了临沅县、沅陵县、临湘县、湘阴县、湘南县等,由此可见沅江、湘江在县域政区命名的重要作用。晋以后,湘江流域在地方行政的重要的地位进一步提升,晋朝廷将湘江流域为主的八个郡(长沙、衡阳、湘东、邵陵、零陵、营阳、建昌、桂阳)合为一个州,名“湘州”,州治为“临湘”(即今长沙)。两晋时期设立的“湘州”在行政地理上很重要,它不仅是将湘江流域归于一体的州级行政单位,“湘”的命名也具有文化地理的特殊意义,强化了“湘”在文化区域概念形成中的重要地位。
这段时期,湖南地区的文化地理的命名而不太一致,但用得较多的是两个:南楚与沅湘。楚国是春秋战国时期的大国,楚文化本身有东南西北的地区差异,故而司马迁在《史记》中谈到“南楚”的区域文化概念,并讨论了其风俗民情的特点,他说:“是南楚也,其俗大类西楚。……故南楚好辞,巧说少信。”[9]所以,“南楚”的区域文化概念沿用很久。就在唐宋以后,仍有许多文人学者沿用“南楚”的区域文化概念来表述及其周围的区域文化命名。“南楚”的区域文化概念出现有其道理,但是不宜作为湖南地区的通用文化地理概念:其一, “南楚”的空间外延不一样,司马迁的“南楚”是指衡山、九江、江南、长沙等郡,包括了后来的湖南、江西等;其二,“南楚”的时间外延也不一样,楚文化与春秋战国时的楚国相联系,有特定的时间范围,最多只能延续到两汉;其三,由于时间外延的差别,故而其文化内涵也有重大区别。所以,“南楚”可以作为楚汉时期的阶段性命名,而并不是一个关于湖南地域文化的通用命名。
战国以来还有一个比较重要的文化地理名称:沅湘。这个命名是以湖南区域范围内两个重要的自然地理标识沅江、湘江为文化地理的标识。最早以沅湘作文化地理标识的是屈原。屈原被贬后,流放到南楚的洞庭、苍梧两郡,即沅水、湘水流域,也就是后来的湖南省区范围之内。屈原流放于沅水、湘水一带,留下了大量的诗歌作品,而作为自然地理标识的沅水、湘水也就大量进入到屈原的诗歌之中:
济沅湘以南征兮,就重华而陈词。(《离骚》)
令沅湘兮无波,使江水兮安流。(《湘君》)
浩浩沅湘,分流汩兮。(《怀沙》)
“沅湘”一进入到屈原的诗歌作品中,就不仅仅是自然地理的标识,而是具有深厚的文化意义了。一方面,“沅湘”概念代表了沅水、湘水流域的本土文化,即所谓“其俗信鬼而好祀,其祠必作歌乐鼓舞以乐诸神”;另一方面,屈原诗歌中的“沅湘”又与诗人的“怀忧苦毒,愁思怫郁”及“上陈事神之敬,下以见己之冤结,讬之以风谏”[10]相关。由此可见,“沅湘”在这里又是一种文化地理的标识,它代表的是一种沅湘本土的苗蛮文化与南下的荆楚文化的结合。此后,“沅湘”遂作为既是自然地理、又是文化地理的标识,出现在各种历史典籍之中。如《前汉书》为司马迁作传时说:“(司马迁)二十而南游江淮,上令稽,探禹穴,窥九疑,浮沅湘,北涉汶泗,讲业齐鲁之都,观夫子遗风。”[11]这里记载的是司马迁对中华大地历史文化的考察,故所谓“浮沅湘”主要是以“沅湘”为文化地理的标识与概念。
“沅湘”作为文化地理概念,也有相对应的行政地理空间。具体而言,它具有与“洞庭苍梧”相对应的行政地理空间。司马迁《史记》记载苏秦所说的楚国“南有洞庭、苍梧”的说法,南楚地区有洞庭郡、苍梧郡,洞庭郡的管辖范围主要是沅水流域,而苍梧郡的管辖范围主要是湘水流域。“沅湘”从自然、文化两个方面来看均是联系紧密的,洞庭、苍梧两郡作为南楚地区也是紧密联系,故而史书上总是将“洞庭苍梧”联系起来说。这充分证明,“沅湘”的文化地理概念的空间外延,与“洞庭、苍梧”的行政地理空间是对应的。
“沅湘”的文化地理概念形成于战国时期,其空间外延与楚、秦的行政区“洞庭、苍梧”相对应,那么,“沅湘”文化的内涵是什么呢?我们从汉王逸的《楚辞章句·序》中,可以分析、发现其文化特性。王逸说:
九歌者,屈原之所作也。昔楚国南郢之邑,沅湘之间,其俗信鬼而好祠。其祠,必作歌乐鼓舞以乐诸神,屈原放逐,窜伏其域,怀忧苦毒,愁思沸郁。出见俗人祭祀之礼,歌舞之乐,其词鄙陋,因为作《九歌》之曲。上陈事神之敬,下见己之冤结,托之以风谏。故其文意不同,章句杂错,而广异义焉。[12]
这里,我们可以明显看到,沅湘文化包含着两个层面。其一,是沅湘流域的民间文化,沅水、湘水流域的居民是上古三苗之后、南蛮之民,与中原华夏族后人深受周孔之教的政治礼仪、道德理性不同,“沅湘之间,其俗信鬼而好祠,其祠,必作歌舞以乐诸神”。也就是说,这是一种充满原始宗教的信仰、具有巫风歌舞的野性的沅湘民俗文化。其二,是屈原在沅湘流域创造的《九歌》、《离骚》等诗歌艺术文化。屈原作为一个伟大的诗人,他在放逐沅湘之时,创作了一大批熠熠闪耀的文学艺术作品,形成了与中原文化的诗歌艺术代表《诗经》并列的南楚文化的诗歌艺术代表《楚辞》,他因此而成为楚文化和中华文化的最杰出代表。所以,沅湘文化又是一种表达了战国时期追求政治理想、道德情操的士大夫精神及其文学艺术作品。
沅湘文化(或南楚文化)内涵的最大特点,是上述两个层面文化的渗透、融合。区域文化的建构、发展,正需要借助于两种文化互动:一是不同区域文化之间的交流互动,二是民间文化与士大夫文化之间的交流互动。而沅湘文化之所以具有那么丰富而深厚的文化内涵,恰恰在于这两点。其一,沅湘文化的形成是区域文化交流互动的结果。屈原追求的政治理想与道德理想来自于中原,他的“重华情结”表达了他对中原圣王舜帝的崇敬,因此,当他“济沅湘以南征兮,就重华而陈词”时,正如杨义先生所指出的:“这是中国诗中第一次出现沅水与湘江,而且把沅湘与中原五帝之一的舜帝联在一起,这一点在中华文化共同体中留下了极有意味的一笔。”[13]这种“意味”就是体现了沅湘文化与中原文化的融合,正是这种区域文化之间交流互动,促进了沅湘文化的提升与发展。其二,沅湘文化的内涵体现了民间文化与士大夫文化之间的交流互动。屈原的《九歌》,显然是源于沅湘流域的民间宗教艺术,但又体现了士大夫精英文化对民间艺术的提升。王逸的说法“如实揭示了《九歌》渊源于湖湘巫歌,而又超越巫歌,进而融合文人的才学灵感的精神创造的诗歌史独立过程。”[14]
沅湘文化作为一个重要的文化地理概念,既有其沅、湘流域的空间外延,又有上述两个文化层面的内涵。那么,这一区域文化形态的时间外延是什么?或者说它持续了多久呢?应该说,“沅湘”与“南楚”的文化内涵和外延是比较接近的,[15]它们所包含的主要是从战国到两汉时期的湖南地域文化。唐宋以后,文人学者开始大量使用“湖湘”的地理概念。
3
唐宋以来“湖湘”文化地理概念的确立
当代人们普遍使用的文化地理概念——“湖湘”,是在唐代出现、宋代盛行的。唐宋时期的学者文人之所以要用“湖湘”作为湖南文化地理的标识,而代替了“沅湘”的标识,这其中既有行政地理的原因,又有文化地理的原因。
“湖湘”作为一个地理概念,最早出现于唐代。如果从电子版《四库全书》中检索“湖湘”一词,就可以发现唐代文献中已经将“湖湘”作为自然地理和文化地理的名称或标识。现从集部中例举几条:
“虽复苍梧北望,湖湘盈舜后之歌;绿荇西浮,江汉积文妃之颂。”[16]
“伏以湖湘旱耗,百姓饥荒,遂有奸凶敢图啸聚。”[17]
“今以湖湘梗涩,伊洛迢遥……”[18]
这几条均涉及“湖湘”的地理概念,可见唐代已经开始较多地用“湖湘”指代洞庭湖以南、湘江流域,这其中尤以王勃的“湖湘盈舜后之歌”比较重要,不仅是因为它出现得最早(初唐),而且具有较突出的文化地理名称的含义。另外,在史部的《旧唐书》、《新唐书》中亦有几处“湖湘”。可见,从唐朝开始,“湖湘”逐渐成为区域文化的标识,与“江汉”、“荆汉”、“伊洛”等地域标识区别开来。
到了两宋,“湖湘”作为文化地理名称普遍地流行开来。同样从电子版《四库全书》中检索“湖湘”,可以看到两宋时期关于“湖湘”的文献资料大大增长,光集部的宋人文集中就可以找到三百多处,在《宋史》中可找到37处。这既体现了“湖湘”地区地位的提升,也反映了人们对“湖湘”标识的普遍认同。尤值得注意的是,两宋时期以“湖湘”为文化地理标识表现出这样的特点,即是将“湖湘”与“荆楚”并列。湖湘地区在战国时期属南楚,故而先秦以来人们往往以“楚”称其文化,即“南楚文化”。但是,从两宋以来,学者往往将“湖湘”与“荆楚”并举。试看以下几例:
“当是之时,战士不过数万,北御契丹,西捍河东,以其余威开荆楚,包湖湘,卷五岭,吞巴蜀,扫江南,服吴越。”[19]
“先平江、淮,静湖、湘,復荆楚,通武关之路,出秦、陇之田,下巴、蜀之粟,一统西南,亘江、汉而北,以壮兵势。”[20]
“汴梁淮泗之郊,荡为榛棘;荆楚湖湘之地,尚厌干戈。”[21]
上面引文中的“湖湘”,均是与荆楚以及巴蜀、吴越、五岭、江南并列的区域。早在唐初,王勃已经将湖湘与江汉并列为两个区域,但是到了两宋时期文人学者和《旧五代史》那里,已是明确将“湖湘”从荆楚之地中分离出来,使之成为一个相对独立的区域,这反映了洞庭湖以南的湘江流域地区地位的大幅提升以及作为独立文化区的形成。
唐五代以来,“湖湘”作为文化地理的名称出现,特别是两宋时期大量历史文献以“湖湘”为区域标识,并以其区分“荆楚”,这有着行政地理与文化地理变化发展的双重原因。
其一,“湖南”行政区的出现所导致的行政地理的变化。战国、秦汉时期所流行的沅湘文化,以洞庭、苍梧二郡为行政地理的依托。两晋时期设立“湘州”,管辖湘资流域的长沙、衡阳、湘东、零陵、邵陵、桂阳诸郡,唐广德二年(769年),设“湖南观察使”,管辖潭州、衡州、邵州、永州、道州。以后的宋、元、明时期,“湖南”就成为统领湘资流域的重要行政单位。可见,楚、汉时期以 “苍梧”命名的湘水流域,遂以“湖南”的行政命名所取代。唐代开始出现、宋代十分流行的“湖湘”标识,与这种行政区域的格局是密切相关的。当时所讲的“湖湘”总是与“湖南”的行政区域空间是一致的。譬如,他们总是将“湖湘”与“湖南”等同使用,黄庭坚《山谷集》载:“《竹枝词》本出三巴,其流在湖湘耳。《欸乃》,乃湖南歌也。”[22]他所说的“湖湘”与“湖南”是同一个空间范围,“湖南”是正式的行政区名,而“湖湘”则主要是自然地理和文化地理的命名。因此,宋人肯定“湖南”政区与“湖湘”文化区二者是同一空间范围。譬如,南宋时期荆湖南路统领5州(潭、衡、道、永、郴)、1府(宝庆)、2军(武冈、茶陵)、1监(桂阳),合计是9个郡级单位。而南宋时任湖南安括使的真德秀在其《潭州谕同官咨目》中说到:“则湖湘九郡之民,庶乎蒙赐。”[23]真德秀说的“湖湘九郡”,与荆湖南路统领的九郡是一致的。当然,这也说明宋人所讲的“湖湘”区域,是不包括沅水流域的武陵、卢溪(辰州)、澧阳、巴陵等郡的。这是唐宋以来人们喜欢以“湖湘”以代替原来更广泛的“沅湘”的原因。
其二,文化内涵的变化。“湖湘”的文化地理空间发生了变化,同时其文化内涵也发生了变化。“沅湘”所标志的文化,是以南下荆楚文化与本土苗蛮文化的结合为特征,尤以屈原及其《楚辞》的特色与成就为标志;而“湖湘”所标志的文化,则是南下的中原文化与本土的楚蛮文化的结合,而尤以理学开山周敦颐及其湖湘思想学术的特色与成就为标志。所以,宋代士大夫眼中的“湖湘”,就与湖湘地区理学家群体的崛起、书院教育的发达联系在一起。他们反复说:
“考诸近世,倡明正学,以绍孔孟之传者,前后迭出,率在湖湘间。至于登朝著仕,州县胜科第者,又不可胜数。”[24]
“窃惟方今学术源流之盛,未有出湖湘之右者。盖前则有濂溪先生周元公,以其心悟独得之,……中则有胡文定公,以其所闻于程氏者设教衡岳之下,……其子致堂、五峰二先生又以得于家庭者,进则施者用,退则淑其徒,……近则有南轩先生张宣公寓于兹土,晦菴先生朱文公又尝临镇焉。……故人材辈出,有非他郡国所可及。”[25]
魏了翁、真德秀是南宋后期两位著名的理学家,他们均非湖南人,但从他们对湖湘文化的论叙与评价来看,两宋时期的文化特质、文化地位均发生了重大变化。其一,就文化特质而言,两宋时期的文化人及他们关注的重点是“绍孔孟之传”、“扶皇极正人心为本”、 “进则施诸用,退则淑其徒”等儒家内圣外王之道、身心性命之学,这与沅湘文化的“信鬼好祠”、“舜帝湘妃”的神话传说、诗歌艺术传统大不相同了。其二,就文化地位而言,在中国文化重心南移的大背景下,两宋时期湖湘文化的地位发生了巨大的提升。从秦汉到隋唐,湖湘地区一直是中华文化演变发展的边缘地区;但到了两宋时期,湖湘学人“倡明正学”,从而导致“学术源流之盛,未有出湖湘之右者”、“有非他郡国所可及”。也就是说,湖湘已成为中华学术文化的核心地区,湖湘学术文化已经成为中华的主流文化。
区域文化总是在历史变迁过程中累积而成,故而区域文化的内涵也会呈现一种层叠的状况,像地质层所体现的年代差别一样。沅湘文化(南楚文化)时期,其文化层叠也分为本土的苗蛮文化和南下的荆楚文化,以及二者融合的楚辞文化。宋代以后,湖湘区域文化的层叠又发生了变化,苗蛮文化与荆楚文化融合的“楚蛮文化”,成为湖湘地区的民间文化与底层文化,而宋代士大夫所讲的“方今学术源流之盛,未有出湖湘之右者”、“绍孔孟之传者,前后迭出,率在湖湘间”的湖湘文化,则成为湖湘地区的上层文化与知识精英文化。如果说,在南楚地区的沅湘文化中,还出现了苗蛮文化与中原文化融合而成的楚辞艺术世界,这是“民间智慧进入文人传统”的典范,是“一个散发着沅湘民俗的清新感和神妙感的精神家园”(杨义语);那么宋以后湖湘文化体系中的楚蛮民俗文化与儒学精英文化之间的关系,则会复杂得多。一方面,外来的湖湘精英文化与本土的湖湘民俗文化之间有着激烈的冲突对立,宋代士大夫在湖湘地区传播中原正统儒家文化时,曾对湖湘本土的楚蛮习俗采取禁抑、压制、改造的政策,他们的“毁滛祠”、禁恶俗等激烈行动,常常体现出湖湘文化的转型、建构过程中两种文化的冲突。另一方面,湖湘精英文化与民俗文化之间又有交流、融合的一面。儒家士大夫对湖湘本土楚蛮习俗的禁仰与压制,是为了建构与正统儒学相一致的礼俗文化。譬如,他们强化了对合乎主流文化观念的祭祀,大量修建神农炎帝、舜帝、屈原、贾谊、柳宗元等儒家圣王、圣贤的祠庙,以取代楚蛮宗教习俗中鬼神系统。但是,他们在关于炎帝陵、舜帝陵、湘妃祠、南岳祠、屈子祠、贾太傅祠的祠祭仪式及活动中,又大量汲收了本土的民间宗教、楚蛮习俗。这又充分体现出湖湘精英文化与民俗文化之间的融合。
4
清朝至近代:“湖湘”文化地理概念的发展
当代学者所讲的“湖湘文化”,其空间外延是在清代确立、成型的。从清康熙开始,才建立起一个融湘、资、沅、澧四水为一体的独立行省即“湖南省”,这是今天我们长讲的“湖湘文化”完全成型的行政地理条件。
从自然地理和文化地理的角度看,湘、资、沅、澧的区域整体性很强。所以,楚汉时期的沅湘文化,是包括湘、资、沅、澧四水流域的。但是,从楚汉至元明,湘、资、沅、澧从未成为一个独立的最高行政单位。从楚国的“洞庭”、“苍梧”两郡分设开始,到两汉以来湘资流域和沅澧流域基本上分属不同的州郡。唐代中期的湘资流域、沅澧流域大体上分属江南西道与黔中道。唐代后期开始出现“湖南观察使”的行政设置,但轄区仅仅是湘、资流域的5个州,沅澧流域则属于另外的团练使或节度使。宋代沅、湘两区域亦分属荆湖北路、荆湖南路。所以,这段时期特别流行的“湖湘”地域,无论是从行政地理、还是文化地理而言,均主要是指湘资流域。这一局面延续到元、明两代。
以“省”为最高一级地方行政区始于元朝。元、明时期,湖南与湖北合为“湖广行省”,省府为武昌。清康熙三年(1664年),作为独立的最高地方政区——“湖南省”正式建立,[26]省府长沙,湖南成为中国内地18省之一。湖南省下设长沙、宝庆、衡阳、永州、辰州、常德、岳阳、郴州、靖州共九个府州(后来,府、直隶州又有一些微小的调整),从而形成了延续至民国的最高一级地方行政区域。这样,湘、资、沅、澧的四水流域也就完全成为一个独立的地方行政区域。
清初以“湖南”命名设立独立行政省区,对区域文化的形态的完全成型也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唐宋以来,人们所说的“湖湘”,往往泛指洞庭湖以南的湘水流域,大多不涉及沅水流域。而到了清朝,人们所说的“湖湘”则包括湘、资、沅、澧四水流域,与楚汉时期所说的“沅湘”大体接近。所以清代时候的“沅湘”往往等同于“湖湘”。如道光23年新化人邓显鹤编一部湖南范围的“诗征”,即取名《沅湘耆旧集》,当时人们的普遍看法,“沅湘”也即是“湖湘”,也就是清朝的“湖南省”的行政区范围。邓显鹤特对取名“沅湘”作出说明:“湖以南水,《禹贡》言九江,《国策》言五渚,实则沅、湘、资、澧四水而已。而资水入湘,澧水入沅,湘长于东,沅雄于西,故举沅湘而湖以南水尽在是,即湖以南郡县尽在是。其曰《沅湘耆旧集》,即《湖南诗征》之变名也。”[27]他特别表明“沅湘”的文化地理范围也就是湖南的行政范围。兵部尚书的裕泰为《沅湘耆旧集》作序时也说:“盖湖以南言诗家尽在是矣,……余以湖湘为风雅故乡,是集为湖湘掌故。”[28]他从文化地理的角度看,认为“沅湘”即“湖湘”,《沅湘耆旧集》即“湖湘掌故”,当然,邓显鹤编湖南地区诗歌总集,所以命名《沅湘耆旧集》,显然是因为楚汉时期的“楚辞”影响太深、地位太重要,才沿用了屈原、贾谊、司马迁以来的“沅湘”的习惯用法。应该说,清代的学者文人更普遍地使用的文化地理标识仍是“湖湘”。
从清初到近现代,以“湖湘”作为湖南地区的文化地理标识一直在沿用,其空间外延也一直保持不变。人们普遍认同湖湘文化是一独立的区域文化形态,这一方面是由于清初建立独立的湖南行政省一直延续到民国以后的今天,另一方面也是由于这一区域文化形态的内涵、特质的连续性。
但是,从清初到近代,这一段时期既是湖湘文化的成型期,又是湖湘文化的转型期。
首先,我们探讨清代湖湘文化的定型。清代湖湘文化的定型,首先是指空间外延方面的,即由于湖南最终以一个独立行政省区的建立,而且将辖区定型为湘、资、沅、澧四水流域,就与楚秦时期的“洞庭、苍梧”、“沅湘”的地理概念保持了一致,构成了一个既有历史渊源、又有时代变迁的区域文化空间。其次,湖湘文化定型又是指文化内涵方面的,即这个时期的湖湘文化,是先秦以来各个时期历史文化的积淀、汇聚,既包括蛮风楚习的民俗文化,也包括湖湘道脉的思想学术。在民间通俗文化方面,清代湖湘仍然保存、沿续了上古苗蛮部落、南楚方国的习俗、宗教、艺术等民间通俗文化,特别是在文化交流不太剧烈的湘西、湘中、湘南地区的民俗文化,更是具有浓郁的蛮风楚习。而在士大夫的精英文化方面,清代湖湘则明显继承了两宋以来以“理学之邦”自居的传统,清代湖湘的主流学术思想一直是理学,清代湖南书院的学风也是理学。总之,两宋盛行的理学,到了清代,已经深入地渗透到湖湘士大夫的思想观念、学术研究、社会政治、家庭生活、学校教育等各个文化层面。
当然,与两宋时期一样,清代湖湘地区的精英阶层的思想文化与民间社会的通俗文化之间,也是一种既有差异、排斥又有交流、互动的关系。主流思想的理学及国家宗教观念等思想文化,正通过社会教化、宗法家族、文学艺术、宗教崇拜等各种途径渗透到民间社会,对民间通俗文化产生影响。同样,民间的文化习俗、宗教观念、文化艺术也会影响湖湘的精英文化。特别湖湘士人表现出来的精神气质现象,十分明显地体现这种民俗文化与精英文化的渗透与组合。一方面,湖湘士人深受楚蛮的强悍民风、刚劲气质的影响,故而具有坚强的血性意志;另一方面,湖湘士人又深受湖湘理学思想传统的影响,坚持儒学正统的价值观念及经世致用理念。这两种的结合、渗透深刻地影响了湖湘士人的精神气质,并且使得清代湖湘士大夫、士绅更加充分地发挥了主流儒学的文化功能。
其次,我们再讨论晚清、民初湖湘文化的转型。晚清以来,湖湘文化的地位急剧提升,并成为近代中国最有影响力的地域文化之一。恰恰这时中国文化正面临近代化转型,各种新的文化观念、思潮不断涌现,推动着中国传统文化的演进与发展。作为晚清时期居于重要地位的区域文化,湖湘文化在中华文化转型的大背景下有了十分显著的表现。中国近代化过程中,涌现出来的各种新的学术思潮、文化观念,在湖湘文化中均有杰出的代表人物及相应的文化观念。譬如,陶澍、魏源等为代表的经世思潮,影响了晚清文化思想界,推动了晚清社会的变革与文化的反思,以曾国藩、左宗棠、郭嵩焘等人为代表的洋务思潮,他们从科技、教育等方面引进外来的文化;以谭嗣同、唐才常等人为代表的维新思潮,以黄兴、蔡锷、宋教仁等为代表的辛亥英烈,他们从思想观念、社会制度方面学习外来文化;最后,新文化运动中,产生了maozedong、蔡和森、李达等一大批接受、传播共产主义思想观念的人物。清末民初的湖湘知识群体,一方面能够追随社会历史的发展,不断地汲收、传播新的文化观念、学术思想;另一方面又继承了湖湘文化传统,包括湖湘精英文化的传统、民间文化的传统,以及二者结合的湖湘士大夫精神气质的传统。正因为清末民初的湖湘文化具有这种创新性与传统性的结合,故而显示出其强悍的生命力,在中国近代区域文化中独树一帜,写下了辉煌的文化篇章,从而推动了湖湘文化的近代转型。
注释:
[1] 通常将地理分为自然地理与文化地理。这个“文化地理”概念是广义的,它包括狭义的文化地理与政治(也包括行政)地理、经济地理等。本文所说的是狭义的文化地理,故与行政地理、自然地理相对应。
[2] 张晓虹:《文化区域的分异与整合·序》,上海书店出版社,2004年,第1页。
[3] 以前普遍认为,湘江发源于广西兴安县白石乡,在永州零陵区的苹岛(潇湘八景中的“潇湘夜雨”所在)与发源于蓝山县的潇水汇合。2013年5月20日发布的湖南省第一次水利普查成果表明,湘江源头在湖南省蓝山县紫良瑶族乡。具体发源地在该乡国家森林公园的野狗岭,也就是潇水发源地。这一成果,已得到国务院水利普查办和水利部的权威认定。
[4] 张步天:《山海经解》卷5,《中山经》,天马图书公司,2004年,第329页。
[5] 【汉】王逸:《楚辞章句》,《文津阁四库全书》,商务印书馆,2006年,第1066-19页。
[6] 【汉】王逸:《楚辞章句》,《文津阁四库全书》,商务印书馆,2006年,第1066-40页。
[7] 【汉】司马迁:《史记》卷69,《苏秦列传第九》,中华书局,1999年,第2259页。
[8] 周宏伟:《湖南政区沿革》,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21页。
[9] 【汉】司马迁:《史记》卷129,《货殖列传》,中华书局,1999年,第3268页。
[10] 【汉】王逸:《楚辞章句》,《文津阁四库全书》,商务印书馆,2006年,第1066-17页。
[11] 【汉】班固:《汉书》卷62,《司马迁传》,中华书局,2002年,第2714页。
[12] 【汉】王逸:《楚辞章句》,《文津阁四库全书》,商务印书馆,2006年,第1066-1067页。
[13] 杨义:《屈原诗学与湖湘文化》,《湖南理工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4期。
[14] 杨义:《屈原诗学与湖湘文化》,《湖南理工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4期。
[15] “南楚”的空间外延比“湖湘”稍广,还包括江西的一部分。
[16] 【唐】王勃:《益州德阳县善寂寺碑》,《王子安集》卷15,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第106页。
[17] 【唐】杜枚:《贺生摛衡州草贼邓裴表》,《樊川集》卷12,《文津阁四库全书》,商务印书馆,2006年,1085-628页。
[18] 【唐】黄滔:《祭右省李常侍》,《黄御史集》卷6,《文津阁四库全书》,商务印书馆,2006年,第1088-106页。
[19] 王云五主编:《司马文正公传家集》卷20,《奏章三·言拣兵上殿札子》,商务印书馆,1937年,第299页。
[20] 【宋】胡宏:《胡宏集·中兴业》,中华书局,1987年,第218页。
[21] 【宋】仲并:《浮山集》卷7,《贺给事启》,《文津阁四库全书》,商务印书馆,2006年,第1141-814页。
[22] 【宋】黄庭坚:《山谷集》卷5,《王才元惠梅花三种皆妙绝戏答三首》,《文津阁四库全书》,商务印书馆,2006年,第1116-690页。
[23] 【宋】真德秀:《西山文集》卷40,《潭州谕同官咨目》,《文津阁四库全书》,商务印书馆,2006年,第1178-455页。
[24] 【宋】魏了翁:《鹤山全集》卷78,《陶君墓誌铭》,《文津阁四库全书》,商务印书馆,2006年,第1177-266页。
[25] 【宋】真德秀:《西山文集》卷40,《劝学文》,《文津阁四库全书》,商务印书馆,2006年,第1178-452页。
[26] 关于建省具体时期有不同意见。参阅周宏伟:《湖南政区沿革》,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143页。
[27] 【清】邓显鹤:《沅湘耆旧集叙》,《沅湘耆旧集》第1册,岳麓书社,2007年,第4页。
关于建省具体时期有不同意见。参阅周宏伟:《湖南政区沿革》,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143页。
[28]【清】邓显鹤:《沅湘耆旧集叙》,《沅湘耆旧集》第1册,岳麓书社,2007年,第4页。
朱汉民,湖南汨罗屈子书院院长,湖南大学岳麓书院国学院院长,历史学、哲学专业博士生导师,湖南大学学术委员会副主任,岳麓学者领军教授。任国际儒学联合会副理事长、中国书院学会会长、中华孔子学会副会长、湖南省文史馆馆员等。任岳麓书院院长20多年,推动岳麓书院的现代复兴。担任国家重大学术工程《(新编)中国通史》中《中国思想史》主编,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重点项目、国家《清史》学术工程项目等十多项。出版《玄学与理学的学术思想理路研究》、《儒学的多维视域》等著作二十多种。发表论文200多篇。获评国务院政府津贴专家、首届湖南省优秀社会科学专家、徐特立教育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