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蓝军能量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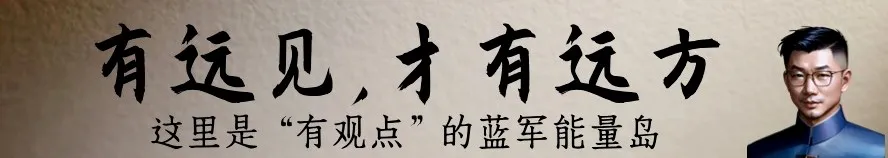
义和团的神话化,本质上是中国近代化进程中「文化身份焦虑」的缩影。柯文引用教育家蒋梦麟的回忆:「洋人既是天使,也是魔鬼」——这种矛盾心理贯穿整个20世纪 。
2025年9月15日,美国汉学家柯文(Paul A. Cohen)在波士顿逝世,享年91岁。作为「中国中心观」的旗手和《历史三调》的作者,他对义和团运动的研究揭示了历史叙事背后的深层文化矛盾——当一场农民 运动被反复改写为「反帝爱国」或「迷信暴民」时,真正的历史反而隐入迷雾。
一、历史学家为何制造神话?
在柯文看来,即使是最严谨的学者也可能无意识地参与神话建构。例如,wenge时期对义和团的宣传虽引用史料,却刻意省略红灯照的「法术」、义和团「刀枪不入」的迷信本质,甚至断章取义地将「视死如归」与「神附体」割裂。这种「选择性真实」并非谎言,而是通过拼凑史料强化某种政治叙事:义和团被塑造成「反帝先锋」,其落后性被掩盖,成为批判现实的工具。
但柯文提醒:神话并非完全虚构,而是现实需求的投射。当西方被视为侵略者(如庚子事变),义和团的抵抗被歌颂;当西方代表现代化(如改革开放),其破坏铁路的行为又遭批判 。这种矛盾心态,正是理解义和团神话的关键。

二、历史与神话的永恒博弈
20世纪80年代后,中国学界试图剥离义和团的政治标签。学者薛衔天对黑龙江canan的重新考证、王致中对红灯照「革命化」形象的解构,都标志着历史研究向实证回归。但柯文指出,新文化运动的「迷信」标签与20世纪20年代的「反帝」美誉,仍是难以挣脱的枷锁。
科学主义困境:将义和团的宗教仪式斥为「迷信」,实则忽视了这些活动对底层民众的心理支撑——在旱灾与压迫交织的年代,「降神附体」不仅是信仰,更是反抗的精神武器 。
民族主义悖论:「反帝爱国」的标签简化了义和团的复杂动机。事实上,其成员既有仇恨洋教的农民,也有被清廷利用的投机者,甚至包含对现代化的盲目排斥。
柯文尖锐地指出:当历史研究被「科学」或「爱国」的宏大叙事绑架,真正的历史细节反而被消解。
三、西方镜像中的中国认同困境

当西方是侵略者:义和团被塑造为民族英雄。例如,1955年东德归还义和团旗帜时,周恩来强调其「反侵略精神」。
当西方是现代化标杆:义和团又被视为「落后象征」。胡适等人认为,其排外行为暴露了中国文化的深层缺陷 。
这种摇摆折射出中国知识分子的困境:如何在学习西方的同时保持文化主体性?柯文认为,义和团的复杂性恰恰反映了近代中国「传统与现代」「本土与外来」的撕裂。
四、柯文的启示:超越非黑即白的历史观
柯文的《历史三调》提出,历史可分为「事件」「经历」「神话」三个维度。对义和团而言:
事件:1900年的暴力冲突、八国联军侵华等客观事实。
经历:拳民的信仰体验、教民的恐惧、普通百姓的生存挣扎。
神话:后世根据不同需求塑造的「反帝先锋」或「愚昧暴民」形象。
他强调,历史学家的使命不是消灭神话,而是揭示其生成机制。例如,wenge时期的义和团叙事服务于阶级斗争,80年代后的批判则呼应了现代化诉求。唯有承认历史解释的多元性,才能避免陷入新的神话陷阱。
结语:在矛盾中寻找真实
柯文的逝世,让我们再次审视历史研究的本质。义和团的「神话迷雾」从未消散,因为它触及了中国近代化最敏感的神经。正如柯文在《历史三调》中所言:「历史的真相,往往藏在不同叙事的裂缝之中」。当我们学会在「反帝」与「排外」、「爱国」与「愚昧」的张力中理解历史,或许才能真正接近那个复杂而真实的义和团。
编辑: 李顺萍